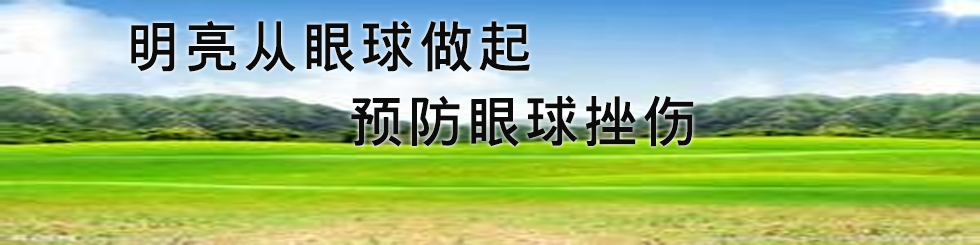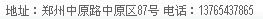|
前一阵子有好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跟我讲到与萨满有关的话题,刚好这段时间我读完了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和刘桂腾的《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两书。借此机会在这里按我的个人理解,对相关知识做一些总结和梳理。一.狭义的萨满萨满一词源自于通古斯语族,例如满语中就有这个词,它用以指称这个族群中一类专司神职的人员。类似的情况在中亚、北亚、北欧以及北美洲北极地区具有高度的共性,在不同民族的语言里这些人有不同的名字,例如蒙古语称“博”“博格”,雅库特语称“奥尤纳”,达斡尔语称“雅德根”等等,我们笼统地总称为“萨满”。以萨满为中心展布开的一系列宗教现象总称为萨满教,狭义的萨满教就是指上述这些地区族群中的一种宗教现象。在这些萨满教社群中,萨满既是巫医又是术士。并且,他们与一般巫医术士不同之处在于其与神灵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即通过癫狂的状态来上天入地,驾驭神灵或使神灵附体。因此,并非任何巫术的使用者都能被称为萨满。下面我主要根据《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从四个方面来稍作详述,包括萨满如何产生、他们与神的关系、典型的萨满活动以及萨满信仰所包含的宇宙观。1.萨满征选与领神萨满征选是指选定某人为萨满的征兆或其本人获得资格的特殊经历,而领神是指准萨满得到认可正式成为萨满的仪式,两者都是成为萨满的必要条件。某种程度上,萨满征选所展现出的特征已经能够充分说明萨满的全部形象了。通常,获得成为萨满的资格有两种路径。其一是通过血缘世袭,但这一路径通常是潜隐的,多是隔代传承甚至是旁支传承。另一个则是神圣召唤或挑选,它以征兆、灾祸、疾病和梦境的形式出现。两条路径很多时候是叠加的,常常相互触发、相互强化。典型的征选可能是这样的:一位曾有远祖成为萨满的年轻人,本身从未考虑过成为萨满。二十岁以前,他总能注意到一些奇异之事,比如在夜里听到空中的谈话声等,但他并未在意。某一天起,他突然开始遭遇连续的厄运和灾祸,诸如雷击、车祸、失业等等;与此同时开始长期生病,时常头痛、产生幻觉甚至癫痫等。他的梦境中会出现自己被撕扯分割的场景,有时又能在梦中见到全世界的景象,乃至见到神灵。梦中常常有神和祖先呼唤他回到族人中去成为萨满。当他下定决心成为萨满后,他的疾病就逐渐好转了起来。这是我一个杜撰的情节,包含了许多征选的要素,包括血缘世袭、神圣召唤和加入式疾病与梦境。整体来说,亦即具有神圣性的精神危机。危机与能力的源头源于家族世袭的萨满才能,它表现为其幼时的异能;但直接原因则是祖先和神灵的挑选和召唤,这通过一个征兆性的体验“雷击”被触发。这些危机至其于死地,而后又使他复生,由此令他具有治疗的能力,根本上来说他的治疗能力来源于治疗自身的崩溃。因此,萨满可以说就是“受伤的医生”,他们因为更能够感受神圣而与神圣结缘,因为更能体悟痛苦而得以治愈痛苦。许多时候萨满在征选中就已经获得了成为萨满的能力和资质。但是征选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化的事,而真正成为族群的萨满还需要得到公众以及萨满前辈的认可,升天而圣化,这就是领神仪式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正是公共表演性的、“教化式”的领神仪式,使不具有普世教会的萨满教得以称“教”,其结构在此得以辨认。领神仪式前通常具有一个很长的准备期。在这个准备期里,除了跟随师傅学习神话、草药、巫术等萨满知识,还要通过特定的方式获得自己的“辅助神灵”。这个过程是萨满死而复生过程的强化或者延续,表现为真实或梦中的旅行、有指导的癫狂乃至“闯关”的形式。此后便举行公开的领神仪式,简而言之就是将萨满的特质用仪式化、戏剧化的形式演示出来。关于萨满“升天”能力的部分常常被尤其强调,许多族群的领神仪式会以爬树、爬杆、上“刀山”、爬绳子乃至爬彩虹(丝巾)等攀爬上升过程为核心。还有一些其它的仪式形式,例如走火炭、钻冰窟窿等等,可概括为“领神磨难”,我认为都是为了展现其自发克服极端条件的能力。领神与征选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征选只涉及个人的体验,而领神仪式则涉及族群的相当一部分人,仪式本身不仅为准萨满个人而设立,也是为了公众关系而存在的。领神中至少有两组关系,一组是老萨满与准萨满之间的师徒关系,一组是萨满与观众之间的圣俗关系。通过领神这一个仪式,此两组关系得以被共同调整和强化。例如,布里亚特人的萨满领神仪式中,引领者被称为“父萨满”,领神者称为“子萨满”。父萨满先会领子萨满们用圣泉的水煮汤,用以为子萨满净化,净化的同时父萨满会开始一番道德训诫:“……为穷人着想,帮助他们……如果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同时召唤你,先去帮助穷人,之后再去帮富人。”(《萨满教》p)此后还会有一些圣祝仪式,接着才是攀爬白桦树的升天仪式。在这里萨满和年轻萨满间的关系被言说为父子关系,以强化师徒间的联结和阶序;同时通过净化和训诫,萨满被安排到族群的社会关系中,并建立起了一个“爱贫”的价值取向。另一个例子中,领神仪式在更大规模上对社群产生影响。铁列吾特地区的萨满领神仪式中,当萨满爬树至第三阶梯时,所有女性和孩子都会离开现场,萨满会开始吟唱带有性意味的歌曲,以这种方式增强在场男性的性能力。(《萨满教》p79)在此,领神仪式针对族群的男性生殖力做出了调整,不仅成为准萨满本人的生命更新,也参与到了族群的更新之中。2.神灵与动物神使与许多朋友想象的不同,萨满教虽是万物有灵论,却并非纯然的“自然崇拜”。在狭义的萨满教流行的地区普遍存在相似的神灵谱系,一般都涉及两类神。例如在我国蒙古族的神话里,一类神被称为腾格里Tangri,即“天”之意,这是一类具有司掌职能的天神,有时也具有一些泛神论的色彩;另一类称为翁衮Ongon,这些神更像是自然精灵,低于腾格里却同样数量庞大,许多是特定的山川、动植物;有些是地方性的,也有些是所有蒙古族群公认的,都具有神像(《中国萨满音乐文化》p)。在雅库特人的神话中,这两类神的地位变得更加对等。天神们高居天上,以位居九级天国的“首席父神”ArtToyonAga为首,无所不能却从不参与人类的事。另一类神居于“下方”,有时与恶魔混同,他们离地面更近,也对人类的事更积极。为首的是“无极全能之神”Ulu-tuyerUlu-yoyon,令人恐惧但心肠不坏,他因为同情人类的苦难而赐予人类火并创造出萨满。他也是鸟兽和森林的创造者,不服从于首席天父(《萨满教》p)。在布里亚特人中,这种划分受到伊朗祆教影响而具有二元神论色彩:存在互相仇视对立的“白可汗”和“黑可汗”两类神,因此也存在服从白可汗的白萨满和服从黑可汗的黑萨满(《萨满教》p)。此处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种对黑白萨满的区分有可能是西方视角下的误读。在蒙古也有“黑白博”的区别。蒙古的黑白之分并不是来源于二元论宇宙观,而是因为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斗争。历史上布里亚特人也曾大规模皈依藏传佛教,作为蒙古部族的一个分支很有可能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两类神基本都不包括祖先灵魂,除非是特别重要的祖先神。许多萨满仪式中也存在祖先崇拜的成分,但并不代表萨满信仰是基于祖先崇拜的。很多时候祖先的加入正说明了萨满的衰落:许多族群中人们认为古代的萨满征选都是由神明召唤萨满的,而近几百年来才变成祖先召唤,这表明萨满的神力进入了一个持续的衰退期。此外,还有一类“辅助神灵”,是能够被萨满掌控的神灵,这些神很有可能就是一些动物的形象。但是,这些神并不是动物,他们只是能变成动物的形态。掌握能力的萨满同样可以变成相对应的动物。动物也会作为神的使者出现,有的时候这个动物就能够代表这位神了,例如鹰很普遍地与至高神相关联。在我了解到的一些因纽特神话里,渡鸦被等同为创世神;但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它只是传递神的话语和任务,或者只是一只有思想的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是满族的祭索罗杆,在此他们将乌鸦视为神鸟。从萨满教的角度说,这并非是崇拜乌鸦本身,而是将其视为天神的使者,因而给予其礼遇。有一些民族的萨满掌握观察鸟群飞行轨迹的占卜方法,很可能索祭罗杆也包含这样的因素。传说中努尔哈赤因乌鸦而得救,将乌鸦视为恩人的说法,很显然是汉化的解释了。除了上述所言,还有一点令我十分在意,也就是在萨满征选和领神中出现的女性守护神,她们作为准萨满“天上的妻子”而存在。这里存在一个十分常见的“仙女下凡”母题。女神或半神的女性下凡与男子结婚,生下孩子后回到天上,丈夫为寻找她而上天入地。有时准萨满与女神的关系变为奥德修斯式的漫游者与指引者(或牵绊者)的关系(《萨满教》p78)。女神在这里并不能够圣化萨满,而是帮助和保护他们,让他们留恋却又必须分离。在如此早的阶段介入萨满的成长过程,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是一种母系的色彩。可能在足够古老的时代,正是由作为主神的女神赋予萨满神圣资格。之所以这样推测,更是因为这里的女神所具有的“动物的伟大母亲”这一典型的母系神形象——女神给予萨满动物形态的辅助神灵,或指引他降服它们;她给予他爱使其成长、复活且因留恋而变成动物。而奥德修斯式乃至吉尔伽美什式的关系则暗示其晚期母系来源,英雄开始违抗女性万能神并向她索要永生,最后又逃离她而去。3.癫狂,上天入地与降神附体癫狂的表现是萨满最典型的表现,这一点从征选开始贯穿始终。萨满的癫狂来自于最初的加入式疾病,但与精神病患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癫狂是可控的。萨满可以控制自己在何时何地开始癫狂,并且还能够自主控制结束它。这种癫狂在日常的清醒中也时有残存,萨满总是表现得情感丰富,记忆力卓越,并且精力充沛,时有怪异举动。他们能够背诵冗长的史诗、族谱,不眠不休地歌舞,能够投入常人不可及的注意力,也能长途跋涉而甚少饮食,甚至吞吃火炭土石。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说癫狂是萨满的专属特征。类似的癫狂可称为“意识状态的改变”,它以“狂喜”“升华”“恍惚”等不同名称存在于许多截然不同的宗教活动之中。这种意识的改变可以由许多手段诱发,例如视觉刺激、冥想、念诵咒语经文、温度刺激乃至于摄入致幻剂。萨满诱发癫狂状态的主要手段是音乐和舞蹈,狭义的萨满是以“通过音乐舞蹈而进入癫狂”为特征的。可控的癫狂是成为萨满的必要资质,但这并不是目的所在——有些宗教活动便单纯以此为目的。癫狂的目的在于分离身体和灵魂,并且能够掌控自身灵魂的行为。这就指向了萨满的总体职能:处理一切与灵魂和神灵有关的事务。因此萨满并不会去主持婚丧嫁娶,却有可能在这些仪式上担任防卫邪灵与巫术的“顾问”。通过癫狂,萨满的灵魂脱离身体,大部分萨满的技艺都以此为基础。例如升天,这是为了与天神沟通,像是亲自送上祭品,这个主题通常通过萨满身披羽毛或者乘坐鸟类得到表现和强化,因为灵魂自然表现为鸟状;或者入地,这是为了指引逝者的灵魂正确前行,这个主题与阶梯和桥相关联(《萨满教》p)。治愈正是利用这个原理,因为生病就是因为病人的灵魂被恶神或怀有恶意的巫师抓走了。萨满需要去天界或地下与之战斗夺回灵魂,例如《尼山萨满》的传说(《萨满教》p)。这个技艺也有一些其它用途,如《巫师:一部恐惧史》中写道,曾经有探险家见过北欧的萨米族部落中,萨满们聚在帐篷里为酋长在雪原里搜寻他遗落的物品,他们虽然身在帐篷,但灵魂已脱离了身体在四处搜寻。有一位萨满突然死去,这是因为灵魂遭受到了袭击;最终萨满们搜寻到了物品,告知了位置让人去取回。所有升天入地乃至战斗搜寻的过程都是在癫狂的歌舞中不断被语言和歌谣讲述的。上述所说的几种技艺,都可概括为“灵魂出壳”,与此相对还有一种逆操作,即召唤神灵前来的降神附体。附体通常需要先使萨满自身灵魂离开,他的守护神灵才能以此为窗口说话;在此之前,他需要歌舞祈祷很久。很多时候,萨满自己的灵魂也会在此同时用他的身体说话,就好像有好几个挤在同一个电话前但人们可以通过声音辨别一样。这种附体不仅可以召唤神灵,也可以召唤其它死者灵魂。不同民族和地区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和细节,风格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原理是类似的,在此不赘述。4.世界之树和星宿崇拜最后简单谈一下萨满教的宇宙观。从上天入地的技艺中,我们已经能够发觉萨满教对世界的描述是一个“三界”的格局,大部分文明都具有这样的观念。在萨满教的神话中,整个宇宙具有一个中心物,就像杆子撑起帐篷一样,是某种耸立之物,它既支撑宇宙,又沟通各个领域。它有许多表现形式,例如宇宙山、世界杆、世界树等等,尤其以世界树的信仰居多,有些民族认为人死后灵魂会以鸟的形态栖息在世界树上。它们所有的仿制品都具有与其类似的意义,这可以通过交感巫术的相似律理解。因此,一座高山和山形的建筑,一棵高大的树,或者帐篷里支撑的木杆都具有了相通的意义,这也就是领神仪式上爬树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满族祭索罗杆的意义。相似律建立起了一个微观宇宙,每个人都可以处在宇宙的中心轴,升天因此成为可能,中心轴的沟通意义也变得更加突出。另一种方式的沟通是通过星辰进入天界,例如楚科奇族认为北极星就是这个天上的空洞,它像帐篷的烟洞一样,萨满能穿过它进入天界(《萨满教》p)。蒙古族也有对北斗七星的信仰,不过这种信仰表现出北斗七星神化生降世的要素却似乎存在汉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狭义的萨满教”并非“原始的萨满教”,也不存在一个萨满教的“标准样态”,所谓狭义指的是限于使用“萨满”这一名词的通古斯语族各族群,以及与其在文化上密切关联的周围族群,范围基本在亚北极地区而以西伯利亚地区为主。许多朋友其实低估了萨满教的融合程度,高估了萨满教的年纪。通古斯语的“?aman”一词,词源来自于巴利语的“samana”,即汉语“沙门”,这在语言学上得到了一定的公认。如今的萨满教形态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全方位的影响,却并未完全融合于其中,可以说它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是协同发展的。可以想象除去了各种外来成分后某种“原初”的萨满教,但这只是一种概念,并不能说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萨满教:即通过癫狂分离灵魂,以升天与天神沟通。在此基础上,通过添加各种要素、调整各部分比重,可以得到现存的各种萨满教形式;但是几乎可以确定,从某个时刻出现“可辨认的萨满教”时,它就是与其它各种要素一同结合出现的了。这些要素并不能说是非萨满教的,例如如今通古斯族的萨满教中升天的比例被降低至陪衬,而附体才是最核心的内容。而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所说的萨满教特征主要在于1.通过音乐癫狂2.通过癫狂分离灵魂3.通过辅助神灵附体或自行升天行使以治愈为主的职能。萨满的能力根植于其创伤性的精神危机,他们为了治愈自己而去治愈他人,为此不断经历意识的崩溃而最终得以驾驭它——文学化地说,在这癫狂之中蕴含着某种崇高。二.广义的萨满此处所谓“广义”萨满,指的是具有某些上述“狭义萨满教”特征但不属于该文化区,或仅仅以底层元素的形式存在于其它宗教文化中的那部分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相似度很高但又不能说一样,具有萨满“色彩”的内容,因此我也称其为“萨满色彩”。《萨满教》一书的作者用专门的篇章比较研究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萨满教,他直接使用了“萨满教”这个词,不过我还是愿意继续使用萨满色彩这种用法。下面我简要地罗列对比一下书中提及的几种“广义萨满”。1.印欧文化中的萨满色彩印欧神话的萨满色彩在神话层面已经十分明显了,尤其是印度神话的“须弥山”和北欧神话的“世界之树”等要素。印欧神的“祭祀/主宰神-武士/战争神-平民/丰饶神”三分系统十分著名,而将其范畴扩大就可以看到类似于中北亚萨满教的二分神系统,例如印度教/佛教中帝释天与阿修罗的对立,还有北欧神话中冰霜巨人与阿瑟神族/华纳神族的对立。不过并不能仅通过这些神话的文本来判断其萨满色彩,因为很有可能是印欧文化的文本影响了中北亚地区,因此还是得看“癫狂”体验的特征以及“升天”的表现。书中罗列了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升天仪式、飞行巫术等要素,以及苦修与加入式的相同之处。某种程度上,印度文化中充斥着萨满色彩,甚至有学者认为萨满教正起源于此。不过印度追寻癫狂的方式却不同,它通过冥想、瑜伽、入定等方式促成“意识的改变”,而其最终目的在于“注视自我”,乃至于“逃离宇宙”。古日耳曼神话以北欧神话为代表,首先就能看到主神“奥丁”名字具有的“疯狂”之意,同时还有他倒悬世界树上九天九夜、献祭眼睛的加入式磨难。与升天入地有关的文本并不是很多见,书中提到其中一部《艾利克斯传奇罗萨》,诗歌描述了一个非常接近萨满降神会的“赛德尔”场面:女先知身穿黑色山羊皮,坐在鸡毛垫子上,在十五对男女的合唱伴奏下恍惚而灵魂升空,预言天气和收成。这个仪式的萨满色彩十分浓郁;与萨满教降神相比,赛德尔尤其着重于占卜预言。古希腊保存的与癫狂和入地有关的文本数量庞大,与直觉不同,似乎萨满色彩与狄俄尼索斯并非相似的癫狂技艺,而与阿波罗和俄耳甫斯密仪存在相当的关系。这部分过于冗长,以后有机会再谈谈。2.中国民间信仰中的萨满色彩书中对于远东地区的研究集中于西藏的苯教以及南方彝族、摩梭族的文化等。我联想到之前读萧梅老师的《田野的回声》,其中有关壮族魔婆做魔仪式的描述,这种宗教文化也有很浓郁的萨满色彩,例如通过恍惚癫狂灵魂出壳,通过巫路升天,处理灵魂事务能够驱使某些特定灵体等等。但是不同之处在于魔婆的癫狂状态并非通过音乐诱发,反而是在癫狂后用连续不断的歌谣说明其升天之旅。汉族也存在具有萨满色彩的宗教活动。山海经中记载有“灵山”、“灵台”,巫咸、巫彭等“操蛇”的十位大巫在此升天:“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巫咸还被认为是鼓的发明者,这些特征十分具有萨满色彩,但缺乏关于癫狂的描述。上古神话中还有有很多天地相通之处,如昆仑山、建木等,但也都不能说是宇宙中心的山或神树。中国古代的升天实践主要被道教的修行所继承,在许多方面都透露出萨满色彩。例如仙人修行的加入式磨难、冬夜卧雪的异能与仙鹤等鸟类的关系以及“羽化”的隐语、调遣神将等等。有些学者考证,道教步罡踏斗的“禹步”姿态正来自于萨满出神癫狂的舞步(一般认为是由禹的跛行姿态而来)。但道教似乎并不追求癫狂、顿悟等意识的改变,而是追求清虚、长生等等。萨满教对汉族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东北地区的保家仙、出马仙以及华北的四大门等宗教活动,这些是能够直接追溯到其满族萨满教来源的。但它们与狭义萨满教相比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鞠熙《城市里的邻居们:北京城内“四大门”动物的生活世界》一文指出,北京的四大门信仰不同于萨满教而是某种“地方动物学”,其崇拜对象直接指向某个特定动物,而非将其视为“神使”,在其之中并不蕴含对某位更高或至高神祇的崇拜,甚至是本着“敬而远之”“礼多人不怪”的态度供奉。对于北京人而言,这些动物并非天然带有神圣性,而是处在一种逐渐高等化的过程中,人也是从与其接触和相处之中进入他们世界的。3.日本的萨满色彩书中主要讨论了日本民间巫女的阿尔泰系萨满色彩。十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萨满的各个要素都几乎能使其称为“萨满教”了,而与亚洲大陆不同的是在日本萨满式职业完全由女性担任。柳田国男的《巫女考》中提到,日本巫女用一种“问汤”的方式来达到出神附体,亦即通过热水蒸汽的温度刺激诱发癫狂。在此我想从文本层面谈一下日本汉化、佛教化程度颇高的神道教记纪神话体系中的萨满色彩。与印欧神话正相反,这里的三分结构虽存在但并不明显,而天津神-国津神二分的体系却一目了然。日本神话的天津神显然比蒙古体系的腾格里们积极得多,而作为最高天神的天之御中主神,或是父神伊邪那岐也一样是隐形、退出的。在记纪神话中,入地被多次提及,首次便是伊邪那岐为了寻找妻子伊邪那美而前往地府。归来后他具备了自己产生神灵的能力,通过净化仪式产生了天照命等三位主神,而天照大神无疑是典型的祭祀王形象。天照大神因为须佐之男作恶而躲入天岩户,象征太阳的死亡;而癫狂在此出现了,天宇受卖命女神通过癫狂的舞蹈引得众神发笑,使得天照女神探出头看,从而使太阳复生,癫狂在此也具有了造成死而复生的作用。此后与入地有关的便是大己贵命被其兄长们逼逃,前往须佐之男所在的根津国,也就是死亡之国。他在这里经历一系列领神磨难式的考验后获得了指引者身份的女神为妻,并偷走了须佐之男的武器,回到人间打败了他的兄长。下一次入地是火远理命入龙宫取鱼钩,与龙女结合的神话。火远理命的母亲木花开耶姬在生下他们两兄弟时将产房点燃,但母子三人却都安然无恙,这也是一个萨满“掌控火”的元素,与踩火炭同理。火远理命在其妻生产时偷看,发现其原型是条鳄蛟,而使得妻子留下孩子回到海中,这又符合上面说到的仙女下凡母题。留下的孩子的孩子就是神武天皇。这一条谱系似乎意在表明天皇世系的萨满-祭祀王身份。其中大己贵命作为出云系的国津神,也具有入地的经历,我的理解是强调其政教军合一的超人权力之意。三.萨满与音声萨满通过音乐和舞蹈来达到可控的癫狂状态,因此音乐的运用对萨满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狭义的萨满正是以通过音乐刺激而癫狂为特征的。同时,在萨满的癫狂与仪式中除了一般意义的“音乐”,还有许多其它声音要素的参与。在此我主要根据《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一书简要地概括萨满音声的特点。1.萨满鼓与腰铃萨满所运用的乐器主要是打击乐器,尤以鼓为主,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法器。萨满鼓的形状很多样,多为圆形和卵形;也有椭圆形乃至接近长方形的。萨满鼓的类型依据持取方式,可以分为抓持式和握持式两类。抓持式的鼓没有手柄,而是在鼓背面有一个十字的绳架,其中心是一个与鼓面平行的圆环,萨满用手抓住这个抓环以持鼓。握持式也就是握住鼓底端延伸出的鼓柄以持鼓。萨满鼓的鼓槌也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棒槌状,用动物毛皮层层包裹;还有一类是细长的竹制或木质长条,用布缠裹,也称“鼓鞭”。萨满鼓上总有着丰富的装饰,这些装饰是萨满观念的符号化,对于萨满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各种兽形的辅助神灵和放射线条状的“神路”。有些鼓的附加部分是有声音意义的,主要是鼓环。鼓环是附加在鼓框上的金属配件,通常是一组金属圆环,也有许多是中国古代的方孔铜钱。在击鼓时摇动萨满鼓,就能运用鼓环增加高频的声音。敲击萨满鼓不同位置,能够发出各种不同音色的敲击音。一般来说,越接近鼓面中心,声音就越低沉,共鸣也越丰富;而越接近鼓边乃至鼓框,音调也就越高,共鸣位置也不相同。萨满通常会将数种音色排列组合为一种节奏型,循环这个节奏型以作为音乐律动的主要骨架。除了鼓以外,萨满还会运用许多响器。最主要的是摇铃,不同民族对此有不同的称谓,如满族称“西沙”、赫哲族称“哈少”等等,大体都是一连串相互倚靠的长条状金属片,使用时将其像腰带一样系在腰和胳膊上,随着舞步规律地碰撞就能发出金属鸣响。这个类型的响器还包括一些球状的金属铃、连缀的铜镜、镶嵌在鞋子上的铃铛。此类响器的发声加入到鼓声的骨架之中,共同构成了层次丰富的打击声层。这类乐器不能依靠手部动作发声,因此将舞蹈与音乐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萨满不可避免地完全沉浸于声音律动之中,可以说其重要性不低于萨满鼓。此外,还有钟形的铃、竹木制的响板和佛乐式的铙钹等响器。萨满几乎不使用旋律乐器。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可以为日本神话中的“八坂琼勾玉”提供解释,即玉石质地的异形腰铃响器。作为单个宝物的“勾玉”常被解释为“丰饶宝石”,但其在神话中的主要作用是“振响”,很明确是一个响器的作用。结合天照命作为祭祀王的身份,可以将其理解为替代神鼓的祭祀鸣响法器,具有召唤和驱邪的意义。顺带一提,作为阿尔泰式萨满的“边缘类型”,日本巫女也会用到一种称为“梓弓”的响器,利用弓弦的点状振鸣声配合问汤引发癫狂。2.神歌鼓与铃及其它响器一同构成了萨满音乐的节奏打击声层,而旋律声层完全由萨满的人声神歌构成。萨满教流行的地区,大多较晚近的时代才有文字传入,因此萨满神歌大多是口传心授,少有文字记录,而对音乐的记录就更少了。从音乐层面而言,萨满神歌有单声的,也有多声的;有些有明确的调式和旋律,有些则没有。多数萨满音乐是单声部有调式的,一般是四声或五声调式,有些没有明确调式的大多由三个音甚至两个音构成,旋律依附于歌词声腔,可能更接近唱念吟咏。满族神歌中有多声部的神歌,栽力子即辅助者配合萨满的歌声一起唱,会使用到大二度的音程,营造出一种空灵而令人敬畏的氛围。有些民族的神歌可能会用到呼麦等喉音唱法,这时也自然会产生多声部。大多数的神歌旋律模式都较简单,运用对句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旋律型后反复循环形成歌曲,而复杂的变化主要产生在歌词中。满族神歌会有一些“神本子”,也就是基本的歌词内容,与祈请神灵、描述升天旅途等内容有关。但这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许多内容都是在歌唱过程中“即兴”的,或是根据癫狂中的情境、集体面临的问题而在当时自然产生的。尽管是即兴创作,歌词也会符合某些文学和音韵原则。一般来说,押韵是最基本的原则。满族神歌有时不仅要押尾韵,还会讲究头韵和中韵。有些中国西南地区苗瑶系统的“广义萨满教”,其歌谣讲究押调,即尾字声调相同,而对韵并不很讲究,这与不同民族的语音特点有关。有时萨满的歌曲和语言会出现十分戏剧性的情景,例如遇到了某位神灵而与他对话,或者辅助神灵通过萨满讲话。所有这些内容也都在歌曲中展开,使歌曲内容变幻莫测。壮族的魔婆做魔时,遇到的神说的任何话都一定是歌曲形式的,因为神灵开口就是歌。即使不是这种情况,萨满也可能与辅助者展开互动。例如满族萨满就会与栽力子对答,此时萨满所唱的内容可能会对栽力子的问话而做出针对性的回答。3.声音的改变此处“声音的改变”是我个人的用词,仿照“意识的改变”构词,我想表述的是萨满对声音的运用能够暗示其灵魂或意识的状态。正如前面说到的,很多人用同一个电话说话,而我们能通过音色辨别他们。当萨满的灵魂发生改变,或有其它灵魂加入时,这种变化也会从声音上体现出来。例如,《萨满教》一书提到,一些萨满会突然开始生动地模仿鸟叫、马叫,同时模仿这些动物的行为,表明自己的灵魂已经变成了鸟或马的形态,或者是鸟形和马形的神灵凭附于他了。许多萨满在被神灵附体时,会用另一种嗓音说话,与其原本的声音完全不同,这就是那位神灵的声音。藏传佛教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一些法事会召请明王附体于喇嘛,此时喇嘛就同萨满一样,通过打击乐的噪音、不断念诵的经文甚至是扼住呼吸而达到癫狂,打了三个喷嚏后明王便附体了。被附体的喇嘛表现得非常急躁、愤怒,声音变得与平时截然不同,说话几乎就是咆哮。有时,并不需要神灵附体,声音也会改变。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萨满做法的视频,其中萨满只是通过出神来占卜,但当这位女萨满癫狂倒地后,声音也变得低沉嘶哑,像是一位老年男性的声音。这可能是身体癫狂的结果,但也正意味着此时萨满并非平时的常人,她所说的话是对未来秘密的透露。四.现代流行文化与萨满萨满教作为一种前现代社会的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里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持续的衰退,在被祛魅的世界中癫狂似乎并没有自己应得的位置。但作为一种被据斥的知识,包括萨满文化在内的广义“神秘学”至少以符号的形式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现代流行文化之中。流行文化对前现代宗教与巫术技艺的符号挪用始终是我热心的一个方向,在此我只能粗陋地放上一些我的观察。根据萨满文化的挪用方式和可见程度,我将现代流行文化中的萨满色彩分为以下三个层面。1.萨满元素所谓萨满元素,即流行文化中对萨满文化最直接可见的视觉形象符号或名称的运用。这在新世纪思潮以来,尤其是新异教运动的影响下,于流行文艺作品中越发多见。许多rpg游戏、slg游戏和moba游戏中都会有萨满或类似的这种职业,意在关联到一种野蛮的、荒野雪原或森林民族的巫术使用者形象。这是萨满形象在流行文化中的基调。例如在魔兽世界中,兽人部落就以萨满教为信仰。在作品中,兽人的萨满教具有某种教义式的道德信条,并且形成了意在抑制“元素之力”平衡自然的组织“大地之环”。这其中也加入了某种环保主义意味的内容,这种“自然守护者”的萨满形象在运用萨满元素的文艺作品中也十分常见,有时也会以“德鲁伊”“先知”“森林之子”等类似名字出现。另一种萨满元素的运用方式与新异教紧密相关,典型的是主打凯尔特德鲁伊教风格、北欧维京异教风格或中亚游牧风格的摇滚和世界音乐乐队。例如实验民谣乐队Heilung乐队,在其MV《Norupo》中,他们“重现”了一个完整的北欧的萨满仪式,展现了三位萨满运用致幻菇和击鼓舞蹈癫狂的仪式场面(可参见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mksmz.com/mbyjg/10881.html |